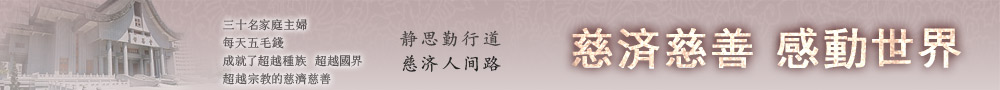李凯:孟子的“天”与列维纳斯的“上帝”
编者按:回望人类足迹,不同国度、不同民族曾以刀光剑影、腥风血雨彼此面对。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间的激烈碰撞,使人类饱受悲苦。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多元文化的交流成为可能。佛与基督,人类最伟大的两大精神导师也开始彼此面对,共聚同存。从2009年开始,佛耶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已举办了三届,会议主办方试图通过学术交流,尝试基督教与佛教之间更深度更积极的对话。交流过程中也曾涉及儒家宗教性方面的话题,西南大学宗教研究所李凯在第二届研讨会上就发表了题为《孟子“尽心知性知天”思想的宗教性意涵新释——以列维纳斯的上帝观为参》的主题演讲,他认为“尽心知性知天”语境中的“天”既可指实存意义上的天,又可指境界意义上的天。境界意义上的天实质上是某种超越之感与无限之感的代称,孟子对超越之感、无限之感的体验是一种宗教体验,这正印证了牟宗三、安乐哲等先生对儒家的宗教性的界定。境界意义上的天与西哲列维纳斯视域中的“上帝”颇具相似性,列维纳斯所信仰的上帝也并非超验实体,而是一个“虚化”的概念。
李凯论文摘要如下:
当代新儒家学者如唐君毅、牟宗三、杜维明、刘述先等多从超越性方面阐发儒学的宗教性意涵。在当代新儒家看来,天是一超越的存在者,是宇宙中的最高实体,人通过道德践履可以契接此实体,由此而展开其宗教实践。
美国著名汉学家安乐哲先生同样着眼于天人关系挖掘儒家的宗教性内涵,但他认为,传统儒家的宗教性在于共同创造性。他提出,“宗教”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指的是人类对充分聚结的理解的追求,以及人类对存在事物的整个场的意义和价值的领会。这即是认为,所谓宗教,是指人从自己的生存境遇中探寻出某种价值和意义,进而用这种价值和意义将自身与天地万物、宇宙整体整合在一起。在他看来,儒家所谓的天是一无限的存在者,是人生存于其中的宇宙整体,而儒家所追求的天人合一便是个人与整体的整合,因而儒家具有宗教性。
安乐哲先生与当代新儒家虽观点各异,且相互论争,但实则他们所概括的宗教性在传统儒家的天论之中皆能找到理据,但又均不尽准确。兹以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之说为例,来说明笔者对儒家的宗教性的理解。
《孟子》载:“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尽其心”之“心”,杨伯峻先生将其直译为“本心”,“本心”是孟子的重要概念,但由于孟子在使用语言的时候并不是十分严格,所以“本心”一语可以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本心是孟子经常提到的“恻隐之心”或者“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四端”合起来是广义的本心。无论狭义的本心,还是广义的本心,都是人类所具有的一种天赋的对于外界刺激的感受性。在许多时候,这种感受性并不发挥作用,而是处于潜伏的状态,但是当它接受到外界刺激之时,它则会展现为某些天然的道德情感。
孟子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的说法显然是在心与性之间建立起了某种本质的、必然的联系,然而本心与本性间虽有密切之关联,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间就必然要画上等号。在孟子这里,性并非独立实体,而是一种属性、一种倾向,它是依附于四端之心而有的,四端之心才是实体。正是因为性依赖于心而有,所以孟子才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意即只有充分地发挥本心的功能,人才能深切地体认到自己内在生命的趋向是一种向善的倾向。
“知性”便可“知天”的说法暗示了性与天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与天之间究竟有何关联关键取决于天为何物。当代学者普遍认为,《孟子》中的天有多重含义,天的含义随语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不过,在谈到与孟子的性善论相关联的天时,学者们大都倾向于认为这个天是义理之天。所谓义理之天,意谓天是人的善良本性的赋予者。孟子称,本心是“天之所与我者”,我们知道,本心是本性所依托者,既然本心是天所赋予的,那么本性自然也是天之所与。孟子的这种说法是渊源有自的。孔子早就说过,“天生德于予”,《中庸》里也讲“天命之谓性”,所以孟子的思路是对儒家传统的继承。无论在孔子那里,《中庸》那里,还是在孟子这里,义理之天都是实体意义上的,是宇宙中的最高存在者,而且这个最高存在者还拥有至善的品格。对孟子而言,这个至善的实体还是心与性的源头,因此,顺着心与性逆流而上,人们就能发现这个天,就能体察到天的善性。因此,所谓“知其性,则知天”,便可以有这样一层含义,即一旦我们人类深切地了解到自己内在生命的趋向是向善的,我们便可以知道这种趋向的赋予者——天也是善的。
由于天的多义性,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之说还可以作其它理解。依笔者愚见,这里的天应当是一种超越之感、无限之感。所谓超越之感,是说四端之心所发出的道德命令超越于感官的欲望、外在的名利之上,令人感到不可违抗。所谓无限之感,是说执行四端之心所发出的道德命令令人充满自信,人们自信道德意志能够指导人生的方方面面,于是感到德性自我遍在万物。
天有超越之感这一层含义,正印证了当代新儒家对传统儒家的宗教性的概括,只不过,当代新儒家在说到儒家的宗教性时,是着眼于作为宇宙生化实体的天,天在其眼中是一“超越实体”,然而超越之感则无实体义,它只在境界中呈现,并无长存不灭、独立不依的特质。天有无限之感这一层含义,则印证了安乐哲先生对儒家的宗教性的说明,只不过,安乐哲先生所说的天指的是宇宙整体,他认为“天人合一”的命题方才体现出儒家的宗教性,而孟子的所谓天本身即为一种上下贯通、内外合一的感受。
天的实体义与境界义具有可以分离的性质,易言之,即使不谈“天是性善的终极根据”,“知天”之说一样可以成立。在这种情况下,“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意为一个人只要坚定地执行四端之心所发出的道德命令,深切地体认到自己具有向善的生命取向,他就能获得一种超越之感、无限之感,就能拥有不为富贵、贫贱、威武所动摇的坚毅和执著,就能拥有与整个宇宙融为一体的阔达与豪迈。
境界意义上的天所展现出的超越性、无限性同样也是儒家的宗教性所在,然而,以往的学者囿于从天的实体义阐发儒家宗教精神的思路,未能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笔者愚见以为,超越之感、无限之感是人类的宗教情感的核心和实质,上个世纪欧洲最伟大的伦理学家列维纳斯正是从这个方面保留了传统犹太教的宗教精神。列维纳斯对犹太思想的改造与其对犹太教宗教精神的保存集中地体现在他的“上帝”观中。
希伯来《圣经》里的上帝是一个“隐身”的上帝,摩西在何烈山初遇上帝时,他看到的是山上正在燃烧却又没有烧毁的荆棘;上帝在密云间对摩西宣讲十诫时,以色列人只能看到电闪和烟气,听到雷鸣和角声。上帝的这种“隐身”的特质被列维纳斯演绎到了极致,换言之,在他的伦理学中,上帝不仅不在人前现身,甚至压根就不存在。列维纳斯宣称,“无神论是与一个真实上帝的确实关系的条件”。无神论者对于上帝的基本态度是认为上帝不存在,在列维纳斯看来,判定上帝不存在恰恰是构筑人与上帝的真正关系的前提。既然上帝不存在,那么“上帝”这个词汇又意味着什么呢?列维纳斯又说,“经由无神论,我们才能找到一个先于对神的否定或肯定的恰当位置”,这个恰当的位置便是,否定神的存在,但保留神的超越性和无限性。这就如同英国学者柯林•戴维斯所概括的,“上帝不是一种本质、实体或存在,因为这些词汇都属于存在论语言;上帝是根本的外在性,是在主体性核心所遭遇的超越性” 。上帝的超越性与无限性被列维纳斯凝练为一个词——“他者”。由于上帝并不是一个作为实体的存在者,因此列维纳斯对他者的指涉更多地落实在“他人”身上,这也就意味着,超越性与无限性实际上是从他人那里体现出来的。对列维纳斯而言,“面向他人的超越性与面向上帝的超越性之间不存在泾渭分明的分别”,既然如此,他人呈现给我们的超越性又是什么呢?列维纳斯说,“他者以他的超越性主宰我,他者是陌生人、寡妇和孤儿,我对他负有义务”,这话就说明了,列维纳斯所谓的超越性是一种超越之感,具体地说,它是自我所感到的他人的诉求超越于我的欲求之上,我必须无条件服从的感受,是他人对我发出的命令令我感到不可抗拒的感受。无限性同样体现自他人。列维纳斯说,“我与无限之间的联系”“存在于我对作为陌生人的他人的临近中”,他人即为陌生人,当我亲近他人时,他人带给我的那种陌生之感就是无限,这说明无限是一种我对他人无法了解的感受。不仅如此,列维纳斯还说过,“强于杀人的是他的脸,在他的脸上已经抵制了我们。这种无限是原始的表达,是第一句话:‘不要杀人’”,这话又说明了列维纳斯的无限之感是一种感到他人不可同化、不可占有的主观感受,所谓“不要杀人”即为“不可同化他人”的隐喻,因不可同化,所以感到他人深不可测、无限深远,这即是无限。
如果上帝只是超越之感与无限之感的代名词,那么列维纳斯又为什么非要选用上帝一词而不是其它词汇呢?这也正是美国学者杰弗里L.科斯基的疑问。他说,“在上帝死了之后,列维纳斯关于上帝的思想因而也只是保留了‘上帝’之名。但是,为什么要保留这个名称呢?通过我上面所讲的一切,看上去我们倒不如抛弃这个名称;一切指向上帝的证词也能够轻易地指向‘非上帝’或者一些别的名称”。
实际上,同样的疑问也适用于孟子,即如果境界意义上的天只是超越之感、无限之感的代称,那么孟子为什么不可以选用其它词汇来对其加以指称呢?依笔者之愚见,“上帝”之于列维纳斯、“天”之于孟子,都是特定文化背景下的选择。在犹太教的传统中,上帝是具有超越与无限特质的,首先,他是一个超越的存在者,他居于高处,不为人所见,但又具有绝对的权威,不俯首听命于他的人必遭他的惩罚,再者,“在西方,‘无限’的概念首先和总是与上帝有关,因为只有上帝才能是无限的,无论是创造的能力还是自身的存在”。同样的道理,在周代的大传统以及由孔子所开创的儒学传统中,天也是具有超越与无限特质的,天是超越的,天命不可违,“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天又是无限的,它无限广大、创生万物,“昊天罔极”,“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总之,无论“上帝”,还是“天”,它们被选作表达超越与无限义的词汇,都不是偶然的,而是相应文化传统中的首选。
不仅“上帝”与“天”都是某种超越之感、无限之感的代称,而且“趋近上帝”的方式与“事天”的方式也是近似的,即都是通过某种人伦道德实践。由于上帝概念是一个虚化的概念,因此,对列维纳斯而言,“趋近上帝”并不是与一个超越的存在者进行互动,而是对他人尽责。列维纳斯认为,与他人对话宛如聆听圣谕,他人所说的内容是自己完全不懂的,是需要虚心领受的,进而听从他人的要求便如同遵守上帝的诫命,听从他人的要求便是对他人尽责。杰弗里L.科斯基指出,“在责任这里,诸如无限、光荣以及超越等概念都显示出了它们的意义”。这就是说,他人带给我的无限之感、超越之感最终都要求我对他人负起伦理责任,承担道德义务。同样地,作为无限之感、超越之感的代名词的天对孟子而言也是虚化的,孟子回应这个天——“事天”的方式也是通过践行人伦道德。孟子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这里的心自然是指恻隐之心等四端之心,性指趋向仁义礼智四德的生命倾向,所谓存心养性便是顺应四端之心的要求而做出“亲亲”“敬长”的道德行为,而履行了对亲与长的道德义务便是“事天”了。综上可知,“趋近上帝”也好,“事天”也好,都只是依顺某种超越之感、无限之感而做出道德的行为。“上帝”或“天”与伦理道德间的这层密切联系也在中西各自的文化传统中有其渊源,具体地讲,希伯来《圣经》中的上帝与人的伦理生活紧密相关,如他曾向摩西颁布十诫,而在孟子之前,中国的天概念也与人的道德有关,如《尚书》中有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之说。不过,既然“上帝”之名与“天”之名分别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产物,这二者便不是可以随意替换的,换言之,“上帝”所含的超越、无限义与“天”所指谓的超越、无限义存在着重要的差别。《圣经》里的上帝始终是高高在上的主宰者,因此列维纳斯以“上帝”指代的超越之感是由外在于我的、不可知的力量时刻压迫于我所造成的,这种超越仍是“外在超越”;而自孔子始,天的人格神色彩被淡化,“天生德于予”的说法开始将外在的天命内化于人,因此孟子以“天”所指代的超越之感是由内在于我的、我能够自觉其存在的道德创造力量不容已地发挥功用所产生的,这种超越是“内在超越”。与此相联系,“上帝”指代的无限之感是一种陌生之感、疏离之感,“天”所指代的无限之感则是亲切之感、合同之感。
超越之感、无限之感是宗教情感的核心和实质,这种宗教情感可以透过对某种超越的存在者的信仰而得以体现,但又不限于此。当然,抛开了某种超验实体的学问体系还不足以谓之宗教,例如杰弗里L.科斯基就针对列维纳斯伦理学而提出,“在责任现象学中所遭遇的宗教式的虔诚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不过,这却无碍于该学问的宗教性。
进入现代以来,面临着科学技术的强势与挑战,现代人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剧变。超验的事物既然超越于经验,便不能在经验领域内得到验证,而现代人对于无法验证的事物往往不予相信。于是,宗教没落了,在西方文化中,“上帝死了”,类似的道理,在中国的知识阶层中,人格神意义上的天乃至实体意义上的天道、天命的观念恐怕也很难复活。离却了宗教,丧失了宗教情感,人们普遍精神空虚、超越诉求得不到满足,行为“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为补救“道德失落”、挽救“宗教边缘化”危机,重新审视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思想所透显出的宗教性意涵,着力维系中国人所特有的宗教情感,恐怕是保持中国的宗教传统的合理选项之一。![]()
相关新闻:
版权声明:凡注明 “凤凰网”来源之作品(文字、图片、图表或音视频),未经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全部或者部分转载。如需转载,请与凤凰网(010-62111406)联系;经许可后转载务必请注明出处,违者本网将依法追究。
- 社会
- 娱乐
- 生活
- 探索
湖北一男子持刀拒捕捅伤多人被击毙
04/21 07:02
04/21 07:02
04/21 07:02
04/21 06:49
04/21 11:28
48小时点击排行
-
108497
1踏雪游少林 感受独特韵味 -
79486
2安徽黄山雪后惊现美丽“佛光” 令人叹 -
78537
3习近平会见星云大师:大师送我的书 我 -
77552
4雪中探访千年古刹南京栖霞寺 银装素裹 -
59620
5沈阳一商场惊现“风衣弥勒佛” 前卫造 -
48772
6素食健康:震惊 肉食背后的25个真相 -
47722
7合肥一楼盘开业请法师祈福 公司领导现 -
36646
8西藏“90后”活佛:用新潮科技概念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