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快乐的人》:第二章
摘自:咏给•明就仁波切 著 《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海南出版社 2013年10月
| 阅读提示:2002年明就仁波切参加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理查德·戴维森主持的实验研究,被测出大脑中的快乐指数在禅定状态中跃升了百分之七百,一度让科学家以为仪器坏了,被美国《时代》杂志誉为“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明就仁波切,在本书中,阐述他自己是如何通过佛法禅修克服童年时代的恐慌症,获得内在真正的快乐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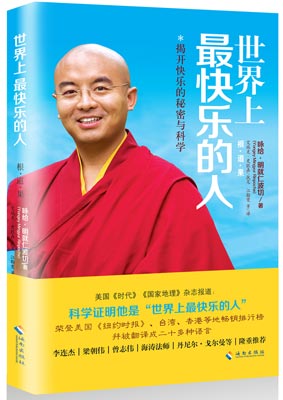
第二章内在的交响乐
许多“组件”的聚集,产生了车乘的概念。——《相应部》(Samyuttanikaya)
身为佛教徒,我最先学到的道理之一,是有情众生——即使是只具有基本觉性的生物,都具有三种基本的面向或特征:身、语、心(编按:传统中文佛教习惯用语为“身、语、意”,本书因应作者的用法,将“意”全部改为“心”,意义相同)。所谓的“身”,指的当然是我们存在的形体部分;身不断地变化——出生、成长、罹病、老化,最后死亡;“语”指的不仅是说话能力,还包括我们用来交流的各种信号,例如声音、语言文字、姿势、表情,甚至信息素,或称为“外激素”,或音译为“费洛蒙”,是哺乳类动物所分泌的一些化学复合物,能够对其他哺乳类动物的行为和发育产生微妙的影响。“语”和“身”一样,都是一种无常的经验,我们透过言语和其他信号所传达的信息不断来来去去,而当身体死亡时,“语”的能力也随之消失。“心”则比较难以形容,它不像“身”或“语”那样,是某种容易辨认的“东西”。无论我们如何深入研究生物的此一面向,都无法真正找到任何可以称为“心”的明确物体。成百上千的书籍和文章都试图描述这难以捉摸的东西,然而,无论我们花费多少时间、精力,企图确认“心”是什么、“心”到底在哪里,却没有任何一位佛教徒,也没有任何一位西方科学家能够下定论说:“啊!我找到‘心’了!它就在身体的这个部位,看起来像是这样,是这样运作的。”
经过几世纪的研究,我们顶多只能确定“心”没有特定的位置、形状、外观、颜色,没有位置(如心脏或肺脏的位置),没有系统(如循环系统),更没有功能范围(如新陈代谢的调节范围)等具体特质,可以让我们将它归入特定的基本生理层面。像“心”这样难以定义的东西,要是能说它根本不存在,那事情就简单多了!要是能把“心”纳入鬼魅、精灵或仙女那类虚幻事物的世界,那事情也简单多了!
但是,又有谁能够真正否认“心”的存在呢?我们能思考、有感觉,能辨认是自己的背在痛或腿麻了,我们知道自己是疲倦或清醒的,是快乐或悲伤的。无法精确指出某个现象的位置或定义某个现象,并不表示这个现象不存在。这只表示,我们累积的资讯还不够,因此无法提出某种可行的模式。打个简单的比方,科学对“心”的了解,和我们对电力这类东西的接受性,两者有什么不同?使用电灯开关或电视,并不需要对电路或电磁有深入的了解。电灯不亮了,你就换灯泡;电视不能看了,就检查一下电缆或卫星连线是否接触不良。你也许得将烧坏的灯泡换掉,也许得把电视与机顶盒或卫星接收器之间的接头拧紧,或把烧坏的保险丝换掉。再不行,就打电话叫技术人员。但是这些行动都依据一项根本的了解或信心:电力是有作用的。
“心”的运作也类似这样。现代科学已经能够辨识出许多形成智能、情绪和感官知觉等心智作用的细胞结构及其形成过程,但是,这些实在都还不足以确认“心”到底由什么所构成的。事实上,科学家们对“心”的活动的研究愈精细,就愈接近佛法对“心”的理解——“心”是一种不断的活动,而不是一个明确的实体。
早期佛教经典的英文翻译,试图将“心”认定为超越当代科学理解范围的一种独特“事物”或“东西”。这些翻译上的不当,源于西方早期的假设,认为所有经验最后应该都和某方面的物理性功能有关。近年来,对经典的诠译则比较接近现代科学对“心”的概念,也就是说,“心”的活动,通过当下经验中不可预测因素与神经元惯性之间的互动而不断进行。
佛教徒和现代科学家都认为,有情或有意识的生物因为具有“心”,所以不同于草或树之类的其他有机体,当然更不同于那些我们不认为有生命的东西,例如石头、糖果纸或水泥块。基本上,“心”是一切有情生物最重要的面向。连蚯蚓也具有心,虽然蚯蚓的心不像人类的心那样微妙和复杂。不过,简单可能也有优点,我可从没听过有哪条蚯蚓因为担心股市而整夜失眠的。
佛教徒与大多数现代科学家认同的另一个论点是,“心”是有情众生本质中最重要的层面。“心”有点像是操作木偶的师傅,而身体和构成“语”的各种沟通形式,则像是木偶师傅手中的木偶。
你可以自己测试一下“心”所扮演的角色:搔一搔自己的鼻子,到底是什么认出了痒的感觉?身体本身能够认出痒的感受吗?是身体指挥自己举起手来搔自己的鼻子吗?身体真的有能力区别痒的感受、手和鼻子吗?再以口渴为例,口渴时,是“心”首先认出口渴的感受,催促你去要杯水,指挥手接过杯子,递到嘴边,并告诉自己喝下去,最后,感受到生理需求获得满足的、愉悦的也是“心”。
虽然我们看不到“心”,但是“心”一直都存在,且不断在活动。“心”是我们辨认不同事物的能力来源,由于“心”,我们才能够辨别建筑物与树木的不同、雨和雪的不同、无云晴空和乌云满天的不同。由于拥有“心”是经验的基本条件,所以大部分人都把它视为理所当然。我们不会特意问自己,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想着:“我想吃,我想走,我想坐下。”我们也不会问自己:“心到底是在身体内,还是超越身体?心是否从某处生起,存在某处,然后止于某处?心有形状或颜色吗?心是否真的存在,或者只是脑细胞基于长期累积的习性而产生的随机活动?”不过,如果我们真的想断除日常生活中经历的各种痛苦、烦恼和不安,并且彻底领会具有心的意义,那么,我们就必须尝试去观看自己的心,辨认它的主要特征。
这个过程其实非常简单。只是一开始时好像很困难,那是因为我们非常习惯于观看充满了有趣事物和经验的“外在”世界。观看自心有点像是在不用镜子的情况下,试图看到自己的后脑勺。
现在,我要出个简单的小测验,示范用一般的理解方式去看待“心”时所产生的问题。别担心,你不会被淘汰,也不需要准备2B铅笔作答。
测验是这样的:下次当你坐下来吃午餐或晚餐时,问问自己:“到底是什么在思考这食物好吃或不好吃?是什么在识别吃的动作?”当下立即的答案很明显应该是:我的头脑。但是,实际以现代科学的角度去看脑时,我们会发现答案并没有那么简单。
脑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一切现象都是心的投射。——第三世嘉华噶玛巴,《大手印祈愿文》
倘若我们想要的只是快乐,为什么需要了解脑部呢?为什么不能只想一些快乐的念头?或想象自己的身体充满了愉悦的白光?或在墙上挂满可爱的小白兔或彩虹图片呢?嗯,也许吧……
不幸的是,试图检查自心时,我们会面临一些重大的障碍,其中一项是根深蒂固且往往是没有意识到的观念:觉得自己“天生就是这样,无法改变”。我自己小时候就体验过这种悲观、无助的感受,和世界各地的人接触时,我也一再看到这样的心态反映在人们身上。即使我们并非故意这样想,但这种“我无法改变自心”的想法,却阻断了所有尝试的意图。
我和一些利用自我肯定、祈祷或观想来改变的人谈过,他们承认,试了几天或几个星期之后,由于看不到立即的成效,他们往往就放弃了。当祈祷和自我肯定都不管用时,他们就把修心的想法当作是一种卖书的行销噱头,将之全盘放弃。
穿着僧袍、顶着响亮的头衔在全球巡回讲学的好处之一就是:通常不可能理会普通人的一些人,都把我当成什么重要人物,乐意和我交谈。和全球各地的科学家对话时,我很惊异地发现,全球科学界几乎都有一个共识:正因为脑部是如此被建构的,所以脑的确可以对日常生活的态度产生实质的改变。
过去十年间,我和神经学家、生物学家及心理学家们的对话,让我学到很多非常有趣的观念。他们所说的内容,有些跟我从小所学的观念有所出入,有些则以不同的角度肯定我所学到的。然而,无论我们是否达成任何共识,我从这些谈话中学到的最珍贵的一课就是:花点时间了解脑部的构造与功能,即使只是部分的粗浅理解,也都能提供更有根据的原则,且有助于从科学观点来了解我身为佛教徒所学到的技巧“如何”及“为什么”有效。
在我所听过关于脑部的比喻当中,最有趣的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神经科学系系主任罗伯特·李文斯顿医生(Robert B,Livingston,M.D.)所提出的。他在1987年“心与生命学会”首次研讨会中,把脑比喻为“一个和谐且纪律良好的交响乐团”。他解释道,脑就像交响乐团,由许多组的演奏者构成,通过共同合作而产生特定的结果,例如动作、想法、情绪、记忆和生理感受等。当你看到别人打哈欠、眨眼、打喷嚏,甚至只是举起手臂,尽管这些动作看起来似乎相当简单,但这些简单动作所涉及的参与者数量,以及参与者之间的各种互动,却形成异常复杂的画面。
我最初几次到西方的旅程中,收到了堆积如山的书、杂志以及其他资料。为了更了解李文斯顿医生所说的理论,我必须请人从书海中帮助我了解这些信息。我发现,其中很多资料实在非常专业。在学习过程中,我不禁对那些立志想做科学家的人和去医学院学习的人相当同情。
幸运的是,我有机会和这些领域的专家详谈,他们把科学术语翻译成我能理解的简易名词。我希望他们也和我一样,从他们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中得到很多益处。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我的英文词汇大增,我也从一般人的角度开始了解脑是如何运作的。当我对关键性细节掌握得更多时,我就愈加清楚地看到:没有佛教背景的人,如果对李文斯顿医生所说的“演奏者”角色和本质有基本的认识,也能了解佛教禅修技巧如何与为什么能在生理层次产生作用。
我热切地想要从科学观点了解自己的脑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我从一个惊惶失措的孩子转变成一个能在全球到处旅行的人,并且能毫无畏惧地坐在几百名前来听我讲学的人面前。我也说不上来自己为什么这么好奇地想知道长年修持能产生变化的生理原因,而我的老师和同辈们大多对于意识的转化本身已感到满足。或许我在前世曾经是个机械师吧。
让我们再回头看看脑部。用非常基本的“一般人”说法,大部分的脑部活动似乎是由一群很特别的细胞所构成,这群细胞被称为“神经元”。神经元是非常喜欢交际的细胞,很爱传话。就某方面而言,它们很像顽皮的学生,总是不停地在传纸条、说悄悄话,只不过神经元之间的秘密对话,主要是关于感官知觉、动作、解决问题、创造记忆、产生念头和情绪等。
这些爱传话的细胞看起来很像树,主干被称为“轴突”,分支则向外延伸,向遍布于肌肉、皮肤组织、重要器官与感觉器官的其他分支及神经细胞传送信息,并接收它们传来的信息。神经细胞通过与邻近枝干之间的空隙传递信息,这些空隙则被称为“突触”。这些信息以被称为神经传导素的化学分子形式负载穿流于这些空隙之间,产生了脑电波扫描器(EEG,或称为脑电图仪)能测量到的电子信号。有些神经传导素现在已广为人知,例如对忧郁有影响作用的血清素,跟愉悦感有关的多巴胺,以及面对压力、焦虑和恐惧时就会分泌的肾上腺素(它也和专注力与警戒性有重大关系)。神经元之间电子化学信号传输的科学专有名词是“动作电位”,这个名词对我来说相当奇怪和陌生,可能跟没受过佛法训练的人听到“空性”时的感受是一样的。
就痛苦或快乐的体验而言,认识神经元活动似乎是无甚紧要,但其中有几个细节却相当重要。神经元彼此联系时,会产生某种类似老朋友之间的连接;它们会养成彼此来回传达同类信息的习惯,就好像老朋友会强化彼此对人、事或经验的判断一样。这样的连接就是所谓“心的习气”的生物基础,类似我们对某类型的人、事物或地方的自动或直接反应。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假设我小时候曾被狗吓倒,那么我脑中就会产生一组神经元连接,一方面出现恐惧感的生理感受,另一方面则出现“狗好可怕”的观念。下次我再看到狗的时候,同一组神经元就会开始交谈,提醒我:“狗好可怕。”这种状态每出现一次,神经元说话的声音就会愈大,而且愈来愈具说服力,直到这种状态成为一种惯性,让我只要一想到狗就会心跳加速、冷汗直流。
但是,假设有一天我到一位养狗的朋友家拜访。一开始敲门时听到狗在狂吠,接着看到它冲出来在我身上闻来闻去,我可能会感到非常害怕。但过了一会儿之后,这只狗习惯了我的存在,于是跑来坐在我脚边或腿上,甚至还开始舔我,快乐又热情到我简直不得不把它推开呢。
狗的反应是因为它脑中有一组神经元连接,把我的味道与它主人喜欢我的各种感受连接起来,而创造了相当于“嘿,这个人还不错咧!”的模式。同时,我脑中跟生理愉悦感相关的一组新的神经元连接,也开始互相交谈,于是我也开始想着“嘿,也许狗是和善的!”之后,每次我再去拜访这位朋友时,这个新模式就会增强,而旧的模式则会愈来愈微弱,直到最后我终于不再怕狗了。
以神经科学术语来说,这种以新模式取代旧模式的能力称为“神经可塑性”,藏文则称之为“雷苏容哇”,可略译为“柔软性”。这两个术语都可以用,听起来也都很有学问。总之,纯粹从细胞的层次来看,重复的经验能够改变脑的运作方式。这就是佛法“如何”能将造成痛苦的内在习性断除,及其背后“为什么”有效的原因。
三脑一体
佛陀的形相分为三种……——冈波巴大师,《解脱庄严宝鬘》
现在我们应该都很清楚了,脑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物体,“是什么在想这食物好吃或不好吃”这类问题的答案,也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即使是像进食或喝饮料这类相当基本的活动,都牵涉到脑与全身几百万个细胞之间,好几千个协调周密、极其迅速(可能才千分之三秒)的电子化学信号交流。不过,在结束脑部之旅之前,我们还要考量脑的另一层复杂面。
人脑中的几百亿个神经元可根据其作用分为三层,每一层都随着物种演化,历经数十万年进化,而成为愈来愈复杂的生存机制。三层中的第一层,也是最古老的一层,是所谓的“脑干”,这是形状看起来像球茎的细胞群,从脊椎神经顶端直接延伸出来。这一层通常也被称为“爬虫类脑”,因为脑干跟许多爬虫类的整个脑部很类似。爬虫类脑的主要作用在于调节基本的、非自主性功能,例如呼吸、新陈代谢、心跳,以及血液循环等,同时也控制所谓的“对抗或逃避”或“受惊”反应。这是一种自动反应,迫使我们诠释突如其来的遭遇或事件是否为潜在威胁,譬如巨大的声响、不熟悉的气味、有东西沿着手臂上爬行,或有东西蜷曲在黑暗的角落等。这个时候,无需有意识的指令,肾上腺素便会开始流窜全身,使心跳加速、肌肉紧绷。如果我们感知眼前的威胁大于我们的胜算,便会逃之夭夭;如果认为自己能击败它,就会挺身奋战。这种自动反应对于生存的重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大部分爬虫类的争斗倾向多于合作,而且没有抚养幼儿的天性,母虫产完卵之后通常就会遗弃巢穴。幼虫孵化之后,虽然已经具备成虫的直觉和本能,但身体仍然很脆弱、笨拙,它们必须靠自己。许多幼虫在出生几个小时之后就夭折了。在爬往各自的安全自然栖息地中(譬如海龟爬向海洋),往往就被其他动物杀死或吃掉了,而且凶手常常还是自己的同胞。事实上,在爬虫类的世界里,父母因为认不出猎物是自己后代,而把新生幼虫吃掉的现象并不罕见。
随着鸟类和哺乳类动物等新种脊椎动物的演化,它们的脑部结构出现了令人惊讶的发展。和它们的远亲爬虫类不同的是,这类新物种的新生儿并没有充分发育到足以照顾自己的程度,所以多少都还需要父母亲的哺育。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并确保物种的生存,脑部的第二层于是逐渐发展出来。这一层称为“脑边缘区域”,它像头盔一样包围着脑干,并纳入了一系列功能已设定的神经连接,能刺激哺育的冲动,也就是提供食物及保护,并透过玩耍和其他活动教导新生代重要的生存技巧。
较高度发展的神经传导路线也赋予这些新物种辨别更大幅度情绪反应的能力,而不只是单纯的“对抗或逃避”。举例来说,哺乳类动物父母亲不仅能够辨认自己幼儿特有的声音,还能分辨幼儿声音所代表的意义,诸如苦恼、愉快、饥饿等。另外,脑边缘区域也提供更广泛且更细致的能力,能“解读”其他动物通过姿势、动作、表情、眼神,甚至微微的气味或信息素所传达的意图。由于能够处理各种不同的信号,哺乳类动物和鸟类因而能够更灵活地适应不断改变的环境,奠定学习和记忆的基础。
我们在稍后讨论情绪的角色时,会对脑边缘系统所具备的惊人结构和能力做更深入的探讨。脑边缘区域有两个结构值得在此特别一提。第一个叫做海马回,位于太阳穴后面的脑显叶。人类有两个海马回,分别位于脑部两侧。海马回对于直接体验的新生记忆扮演着决定性角色,并提供空间、理智和语言(至少对人类而言)的脉络,让情绪反应有意义。脑部这个区域受到损伤的人很难制造新的记忆,对于海马回受伤前的一切,他们记得清清楚楚,但海马回受伤后所遇见的任何人与发生的任何事,他们一瞬间就忘记了。海马回也是脑中最先受到阿兹海默氏症及精神分裂症、重度忧郁症、躁郁症等精神疾病影响的区域之一。
脑边缘系统另一个重要的部分是脑杏仁核,这个神经元结构体积很小,形状像杏仁,位于边缘系统的底部、脑干的上方。跟海马回一样,人类脑中这个小小的器官也有两个:一个在右半脑,另一个在左半脑。脑杏仁核扮演两种关键性角色:感受情绪的能力与制造情绪记忆的能力。许多研究显示,脑杏仁核受损或摘除时,各种情绪反应的能力也几乎都会随之丧失,包括最基本的恐惧冲动和同理心,患者同时也会失去建立或识别人际关系的能力。
在建立实用的快乐科学时,我们必须重视脑杏仁核和海马回的活动。脑杏仁核和两个重要部位相连:一是自律神经系统,是脑干中自动调节肌肉反应、心脏反应和腺体反应的部位;另一则是“下视丘”,是脑边缘区域基部能间接导致肾上腺素等荷尔蒙分泌的神经元结构,因此,脑杏仁核所制造的情绪性记忆非常强烈,和重要的生物与生化反应密切相关。
当某事件引起强烈的生物反应,例如肾上腺素或其他荷尔蒙大量分泌时,海马回就会发出信息给下方的脑干,将这事件当作一种模式储存起来,也就是形成记忆。正因为如此,许多人能够精确地回忆当初听到或看到航天飞机坠毁事件,或肯尼迪总统被刺杀时,自己在哪里或在做什么。极度正面或负面的个人经验,也同样会以记忆的模式储存在脑干中。
由于这样的记忆及其相关模式非常深刻,日后类似事件很容易就会触发原来的记忆,即使有时候事件的相似度相当低。面对威胁生命的状况时,这类强烈的记忆反应显然对生存具有重要的作用:它让我们辨认并避免食用曾经使我们生病的食物,也让我们避免跟攻击性特强的动物或同种成员对抗。但是,它也很可能会混淆或扭曲我们对较普通经验的感知。举例来说,常常被父母亲或其他成人羞辱及批判的孩子,长大成人之后,在面对权威人物时,可能会有异常强烈的恐惧、怨恨或其他不悦的情绪。这种扭曲反应的产生,通常是因为脑杏仁核用于触动记忆反应的连接方式不够精确。只要现在情境中有某个重要因素类似过去经验中的某个因素,就会撩起储存在原始经验中各式各样的想法、情绪、荷尔蒙反应和肌肉反应。
脑边缘系统有时也称为“情绪的脑”。脑边缘系统活动的平衡主要靠“皮质层”——脑部的第三层,也是最新发展的一层。皮质层是哺乳动物特有的结构,具有推理、形成概念、计划,以及调整情绪反应的功能。尽管大部分哺乳动物的皮质层都相当薄,但只要看过猫如何设法撬开衣橱,或看过狗学会如何操作门把手,你就可以见证到动物大脑皮质层的功用。
人类和其他高度进化的哺乳类动物的大脑皮质层,已发展为更大且更复杂的结构。大部分人想到脑时,心中出现的画面通常就是具有许多突起和沟槽的这层结构。事实上,如果不是这些突起物和沟槽,我们根本就无法想象脑部是什么,因为发达的大脑皮质层赋予我们想象力,也赋予我们创造、理解及运用符号的能力。皮质层让我们具有语言、写作、数学、音乐和艺术的能力。我们的皮质层是理性活动的中心,是解决问题、分析、判断、控制冲动,以及组织信息、从过去的经验与错误中学习、同情他人等能力的所在。
仅仅知道人脑由这三层不同的构造所组成的事实,就已经够令人惊讶了。更神奇的是,无论我们觉得自己有多么先进或高度发展,任何一个念头的产生都必须经过脑干、脑边缘区域与皮质层这三层构造之间一系列复杂的互动。此外,每一个念头、感受或经验似乎都是一组不同的互动关系,所涉及的脑部区域也都是独特的,不是其他念头所能启动的区域。
| |
1
2
|
|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凤凰网无关。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
频道推荐
智能推荐
48小时点击排行
-
108497
1踏雪游少林 感受独特韵味 -
79486
2安徽黄山雪后惊现美丽“佛光” 令人叹 -
78537
3习近平会见星云大师:大师送我的书 我 -
77552
4雪中探访千年古刹南京栖霞寺 银装素裹 -
59620
5沈阳一商场惊现“风衣弥勒佛” 前卫造 -
48772
6素食健康:震惊 肉食背后的25个真相 -
47722
7合肥一楼盘开业请法师祈福 公司领导现 -
36646
8西藏“90后”活佛:用新潮科技概念阐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凤凰网保持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