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快乐的人》:第一章
摘自:咏给•明就仁波切 著 《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海南出版社 2013年10月
| 阅读提示:2002年明就仁波切参加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理查德·戴维森主持的实验研究,被测出大脑中的快乐指数在禅定状态中跃升了百分之七百,一度让科学家以为仪器坏了,被美国《时代》杂志誉为“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明就仁波切,在本书中,阐述他自己是如何通过佛法禅修克服童年时代的恐慌症,获得内在真正的快乐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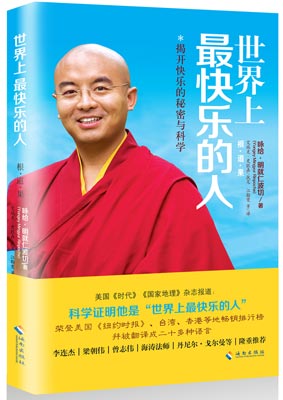
第一章旅程的起点
如果有任何能够因应现代科学需求的宗教,那可能就是佛教了。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如果你是受过训练的佛教徒,那么你就不会把佛教当作一种宗教,而会把它当作一门科学,一种透过技巧探索自身经验的方法。这些技巧让你能以非批判性的方式检视自己的行为和反应,而这些见解能让你逐渐认清:“哦,原来我的心就是这样运作的!我必须这样做才能体验到快乐,不那么做才能避免痛苦的产生。”
基本上,佛法是非常实用的。佛法告诉我们要从事能够助长平静、快乐和自信的事,并避免会引发焦虑、绝望和恐惧的行为。佛法修持的重点,并不在于刻意改变想法或行为,以使自己成为更好的人,而是要认识到,无论你如何看待影响自己生命的那些遭遇,你原本就是良善、完整,且圆满具足的。佛法修持是去认出自心原本具有的潜能,换句话说,佛教注重的并不是让自己变得更好,而是认识到此时此刻的你,就如你自己一直深切期望的,是完整、良善,且本质上是完好健全的。
你不相信,是吧?
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也不相信。
首先,我想坦白告诉大家一件事。打从童年开始,恐惧感和焦虑感就不断困扰着我。每当身处陌生人群之中,我就会心跳加速,冷汗直流。这种状况发生在一位转世喇嘛身上似乎很奇怪,因为转世者累世以来不是已经累积了许多善根善行吗?当时我所经历的不安根本毫无理由可言。我住在一个美丽的山谷,身边围绕的都是亲爱的家人、男女出家众,还有那些致力于学习如何唤醒内在平静与喜乐的人。然而,焦虑感却与我形影不离。
大约6岁时,我这种状况才开始有所缓解。在孩童好奇心的促使下,我开始爬上村落附近的山巅,探索历代佛法修行者终生禅修的各个山洞。有时我会爬进山洞假装自己在禅修,可想而知,当时我对禅修根本就一窍不通。我只是坐在那儿,心里不断持诵“唵嘛呢叭咪吽”——这是几乎所有的藏人,无论佛教徒与否,都耳熟能详的密咒。有时我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心里不断默念这个密咒,虽然我并不了解自己在做什么。但即使如此,我还是开始感受到一股平静感悄悄潜入心中。
往后三年,我就经常在山洞中静坐,试图搞清楚到底该如何禅修。但是,焦虑感仍然持续增强,到最后演变成可能是西方医学所说的恐慌症。有一阵子,祖父会随意地给我一些简单的教导。祖父是一位伟大的禅师,但不愿公开自己的成就。后来我终于鼓起勇气,请母亲代我向父亲祖古·乌金仁波切请求,让我正式跟随父亲学习。父亲答应了,于是在接下来三年之中,他教导我各种不同的禅修方法。
一开始我其实并不十分明白,我努力试着依照父亲所教导的方法安住自心,但我的心就是无法安住。事实上,在正式修学的最初那几年,我发现自己的心竟然比以往更加散乱。让我心烦意乱的事情真的是不计其数:身体的不适、背景的声响,以及和他人的冲突等。多年之后我才逐渐明了,当时的我其实并没有退步,而是变得更具觉知,更能察觉到念头与感官知觉之流相续不断地来去,这是我过去不曾认出的。看到其他人也经历同样的过程时,我终于了解,这是初学者以禅修方法审察自心时大多会有的经验。
虽然我开始有一些短暂的平静体验,但恐惧和忧虑却依然如鬼魅般纠缠着我。尤其是在那段时间,我每隔几个月就会被送到印度的智慧林,和一群陌生同学一起跟随新老师学习,然后再被送回尼泊尔,继续向父亲学习。智慧林是第十二世泰锡度仁波切的主座,而泰锡度仁波切是藏传佛教当代最伟大的大师之一,也是对我影响最深的老师之一。他深广的智慧和无比的恩德引导了我成长,我实在无以回报。我就这样在印度和尼泊尔之间来来去去将近三年时间,接受父亲和智慧林老师们的正式指导。
12岁生日前不久,最恐怖的时刻终于来临了!我被送到智慧林去完成一个特别的仪式,也是我长久以来最最担忧的一件事:以第一世咏给·明就仁波切转世者身份正式升座的坐床典礼。与会者有好几百人,而我明明是个吓得要死的12岁小孩,却得像个大人物般,要在那里连续坐上好几个小时,接受大众的供养,并给予他们加持。好几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我的脸色愈来愈苍白,站在身边的哥哥措尼仁波切(Tsoknyi Rinpoche)以为我就要昏倒了。
回顾这段时光,想到老师们对我的仁慈,我实在不明白自己当时怎么会如此恐惧。现在分析起来,我当时的焦虑其实是因为我还没有真正认识自心的真实本性。虽然我对自心本性已经具有知识性的了解,但缺乏直接的体验;唯有对自心本性的直接体悟才让我真正明白:任何的不安和恐惧只不过是我自心造作的产物,而自心本性不可动摇的宁静、信心和喜乐,其实比自己的眼睛更贴近自己。
在我开始正式修学佛法的同时,一些奇妙的机缘也随着到来。虽然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新发展对我的生命将有深远影响,并将加快我个人成长的速度——我开始慢慢接触到现代科学的观念和新发现,尤其是关于脑的原理和运作方面的研究。
心的交会
我们必须经历这个过程,那就是真的坐下来检视自心,检视自己的经验,才能看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卡卢仁波切(Kalu Rinpoche),《口传宝集》
认识法兰西斯寇·斐瑞拉时,我还是个小孩子。他是一位智利籍生物学家,后来成为21世纪最知名的神经科学专家之一。当时我父亲的名声已吸引不少西方学子,因此法兰西斯寇也来到尼泊尔,跟随我父亲学习佛教审察自心的方法。在课后或修持的空当,他常会跟我谈到现代科学,尤其是他专精的脑部结构与功能领域。当然,他在讲解时,会顾虑到一个9岁孩子的理解能力。父亲的其他西方弟子知道我对科学有兴趣后,也纷纷把他们所知道的生物学、心理学、化学和物理等现代理论传授给我。这有点像是同时学习两种语言:一种是佛法,另一种是现代科学。
我还记得,当时我就觉得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多大差异。语言的表达虽然不同,但意义似乎非常接近。不久之后我也开始体会到,西方科学家与佛教科学家探讨问题的方法非常类似。传统佛教经典通常先提出所要检验的理论基础或哲学基础,也就是“根”。接下来再提出种种修持方法,也是一般所称的“道”。最后以个人实验结果的分析,以及进一步研究的建议作为结论,这通常称为“果”。西方科学的研究架构也很类似,首先提出理论或假设,接下来解释验证理论的方法,最后提出实验结果,并和原先所提假设之间的异同做比较分析。
同时学习现代科学和佛法修持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佛法教导人们以一种内审或主观的方法,明了自身具足获得快乐的能力;西方科学则以一种较为客观的方式解释这些教法“为什么”有用,以及“如何”运作。佛教与现代科学对人心的作用各有卓越的见解,两者并用,可以更为清晰完整。
往返印度与尼泊尔的时期接近尾声时,我得知智慧林即将举办一期三年传统闭关课程,闭关指导上师是萨杰仁波切(Saljay Rinpoche)。萨杰仁波切是藏传佛教界公认最有成就的前辈大师之一,也是我在智慧林最主要的老师之一。温和仁慈、声音低沉的他拥有一种神奇的能力,总是能在最恰当的时间说出或做出最对的事情。我相信你们必定也曾遇见过类似这样的人,他们总是能够让你在无形中学到异常深刻的法教,而他们本身的风范就是让你终生受用不尽的学习。
因为萨杰仁波切年事已高,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指导闭关了,因此我真的很想参加。但那时我才13岁,一般都认为这个年纪还太小,无法承受闭关三年的严苛考验。我恳请父亲出面帮我请求,最后泰锡度仁波切终于允许我去参加这次闭关。
描述这三年的经验之前,我认为需要先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说说藏传佛教的历史,这也有助于说明我为什么如此急于参与闭关课程。
传承的重要性
概念性的知识是不够的……你必须拥有源自亲身体验的确信。
——第九世嘉华噶玛巴,《大手印:了义海》
我们所称的“佛教”,也就是直接探索心及修心的方法,源自一位名为悉达多(Siddhartha)的印度贵族青年所给予的教导。生长于权贵之家的悉达多王子发现,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他一样拥有锦衣玉食的生活。亲眼目睹人们所经历的种种可怕苦难之后,他毅然放弃家庭的安全和舒适,而去寻求解除人类痛苦的方法。痛苦的样貌很多,从挥之不去的“‘要是’生命中这件事不是这样,我就会比较快乐”的轻声埋怨,乃至于病苦、死亡的恐惧,全部都是。
悉达多后来成为一位苦行僧,游走印度各地拜师学习。这些老师都声称已经找到悉达多在寻求的答案,然而他们所给的答案和所教导的修持法,似乎没有一样是真正圆满的。最后,悉达多决定完全放弃外在的寻求,而从痛苦生起的地方追寻解脱痛苦的方法。这时他已经开始怀疑,问题的源头就在自己的心里。他坐在印度东北部比哈尔省菩提迦耶的一棵树下,深入自己的内心,矢志找到他所追寻的答案,死也不罢休。就这样昼夜不停地过了许多天之后,悉达多终于找到他所寻求的不变、不灭、广大无垠的根本觉性。从这甚深的禅定境界中起座之后,他再也不是原来的悉达多了,他成为佛了。在梵文中,“佛”是对“觉醒者”的称呼。
佛陀体悟的是自己本性的一切潜能,而这潜能先前却被二元观限制住了。所谓的二元观,就是认为有某个独立存在、原本真实的“我”,和某个一样也是独立存在、原本真实的“他”,两者是分离且对立的。如同稍后我们会深入探讨的二元观并不是一种“性格上的瑕疵”或缺陷,而是根植于脑部构造和功能的一种复杂生存机制,但就和其他机制一样,是可以透过经验而改变的。
透过向内审察的功夫,佛陀认清了这种改变的能力。往后四十年,错误观念究竟如何深植于心中,以及如何斩断它们,即成为佛陀游历印度教学的主题,并吸引了数百位,甚至可能数千位弟子。两千五百多年之后,现代科学家开始透过严谨的临床研究,显示佛陀通过主观审察所领悟的见解竟然异常精确。
由于佛陀所领悟及感知的境界远远超过一般人对自身及实相本质的认识,因此,就像他之前和之后的大师一样,佛陀也不得不以寓言、举例、谜题和隐喻等方式来传达他所了解的一切。换句话说,他必须使用言语。这些法教最后以梵文、巴利文(Pali)及其他语言记录下来,但也一直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一代接一代地流传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听到佛陀,以及追随他而获得相同解脱的大师们所宣讲的话语时,我们一定会去“思考”这些话的意义,然后把这意义“运用”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会让脑部组织作用产生改变,让我们达到佛陀所体验的相同解脱,为自己创造机会,去体验佛陀所体验到的自在。这些我们会在稍后的篇章加以讨论。
佛陀涅槃后几个世纪,他的法教开始传到包括西藏在内的许多地区。西藏因地理位置与世隔绝,恰好提供了历代师徒能致力于学习和修持的绝佳环境。那些已证悟成佛的西藏大师们将毕生所学传授给最具潜力的弟子,之后这些弟子又将这智慧传授给自己的弟子。于是在西藏建立了一个以“经”(以佛陀早期弟子忠实记录下来的佛陀言教)、“论”(阐释经典的论著)为基础不间断的法教传承。然而,藏传佛教传承的真正力量,在于上师和弟子之间心与心的直接联结。上师将传承的法教精髓以口传,而且往往是以秘密口传的方式传给弟子,这个方法让法教得以如此纯粹而有力。
由于西藏许多区域都被山峦、河川和山谷层层阻隔,往来不便,也使得历代大师与弟子们难以彼此分享所学,不同区域的法教传承因而产生些许不同的演变。目前藏传佛教主要分为四大教派:宁玛、萨迦(Sakya)、噶举与格鲁(Gelug)派。尽管这四大教派是在西藏不同区域、不同时期形成,但各派的基本教理、修持和信念却是一样的。据我所知,四者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名词术语,以及学理与修持方法上的细微差别,就如同基督教新教各派之间的情形。
宁玛派是四大教派中最古老者,创立于公元7世纪到9世纪初期的藏王统治时期。藏文中,“宁玛(nyingma)”一词可大略翻译为“古老的”。不幸的是,西藏末代君王朗达玛(Langdarma)因为政治与个人因素,开始以暴力镇压佛教。公元842年,朗达玛遭人刺杀身亡。虽然他的统治只有短短四年,但在他死后近150年里,早期的佛法传承却一直停留在类似“地下活动”的状态。西藏在这个时期也经历了重大的政治变革,最终重组为一群分立而松散联盟的封建领地。
这些政治变迁提供了某种机会,让佛法慢慢地重新伸展它的影响力。印度大师们千里迢迢来到西藏,而有心学习的学生也不畏艰苦横越喜马拉雅山脉前往印度,直接受教于印度佛教大师。在这个时期,噶举派首先在西藏扎根。藏文“噶(ka)”,可略译为“言语”或“指示”,而“举(gyu)”的原本的意义是“传承”。口传是噶举传承的基础,上师将法教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授给弟子,因此让法教的传承得以保存无与伦比的纯粹。
噶举传承起源于公元10世纪的印度,当时有一位潜能已臻至完全正觉境地的帝洛巴大师。帝洛巴所达到的深刻证悟,以及他达到这些证悟所运用的修持方法,历经师徒相传数代之后,传到了冈波巴大师。冈波巴是一位杰出的藏人,他放弃医生一职,转而追随佛陀的法教,最后将毕生所学全部传授给四位最具潜力的弟子,这四位弟子又在西藏不同区域各自创立了学派。
四位弟子之一的杜松·虔巴(Dusum Khyenpa)创立了今日所称的噶玛噶举(Karma Kagyu)传承。“噶玛”源于梵文的“Karma”,可略译为“行动”或“活动”。在噶玛噶举传承中,记录在一百多部典籍里的学理与实修全套法教,就是由这位名号“噶玛巴”的传承上师亲自口传给少数几位弟子。其中有些是为了将法教完整传给下一世噶玛巴而不断转世者,借此保存并保护一千多年来一直以清净形式流传下来的无数教诫。
西方文化中完全没有这种直接且不间断的传续形式。我们可以想象到的最接近的情景就是,爱因斯坦对他最优秀的学生说:“不好意思,我现在要把毕生所学都倒进你脑袋里,麻烦你保存一段时间。二三十年后,当我以另一个身体回到这世间时,你要负责把我教给你的一切,倒回这个小孩脑海里,而你也只能靠我现在传给你的一些征兆认出这个孩子就是我。哦,还有——为了以防万一,你必须把我现在所教你的一切传授给几个弟子,这样才能够万无一失。至于这些弟子的特质,你只要依照我现在要传授给你的法教就能认得出来。”
第十六世噶玛巴于1981年圆寂之前,将这整套珍贵的法教传给了几位主要弟子,也就是所谓的“心子”,赋予他们将法教传授给下一世噶玛巴的大任;同时也嘱咐他们要将整套法教传给几位卓越的弟子,以确保法教能够完整地保存下去。第十二世泰锡度仁波切是第十六世噶玛巴最重要的心子之一。他认为我是一位具有潜力的弟子,因此促成我前往印度,追随智慧林里的几位大师学习。
前面我已经提到过,各个教派之间的差别其实并不大,通常只是名相与学习方式有少许不同。例如在教导心的本性时,宁玛派所用的名相是“卓千”,藏文意义是“大圆满”,我父亲和我后来的几位老师都被公认是这个传承中成就非凡的大师。而噶举传承,也就是泰锡度仁波切、萨杰仁波切,以及智慧林诸位老师修学的主要传承。关于心的本质的法教总称为“玛哈木札”(mahamudra),可大致翻译为“大手印”。这两套教法之间的差异很小,最大的区别也许在于,大圆满法教着重深入了解自心本性的“见解”,而大手印教法则偏重有助于直接体验心的本质的“禅定实修”。
在这个充满飞机、汽车和电话的现代世界中,老师和弟子们可以方便地到处旅行,过去不同教派之间可能存在的各种差异也不再明显。然而,有件事却一直没有改变,那就是到精通法教的大师那里得到“直接传续”的重要性。通过与一位活生生的大师直接接触,某种珍贵异常的东西会直接传过来,仿佛某种活生生、会呼吸的东西从大师的心传到弟子的心一样。在三年闭关课程中,上师就是以这种方式将法教传给弟子,这或许可以说明我为什么如此急于加入智慧林闭关的原因。
| |
1
2
|
|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凤凰网无关。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
频道推荐
智能推荐
48小时点击排行
-
108497
1踏雪游少林 感受独特韵味 -
79486
2安徽黄山雪后惊现美丽“佛光” 令人叹 -
78537
3习近平会见星云大师:大师送我的书 我 -
77552
4雪中探访千年古刹南京栖霞寺 银装素裹 -
59620
5沈阳一商场惊现“风衣弥勒佛” 前卫造 -
48772
6素食健康:震惊 肉食背后的25个真相 -
47722
7合肥一楼盘开业请法师祈福 公司领导现 -
36646
8西藏“90后”活佛:用新潮科技概念阐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凤凰网保持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