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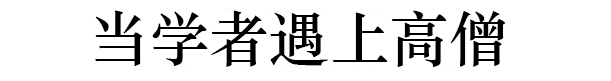

| 末木文美士: | 说起日本的佛教,无论如何都抹不掉与“殡葬”的联系,因此日本佛教被称为“殡葬佛教”。现在,殡葬仪式越来越专业化了。对此您怎么看? |
有马赖底:我认为这种形式也不错。僧侣主要负责为死者家属的“今后”出谋划策,给予心灵的护理和关爱。其实,过去殡葬仪式都是由专业公司操办,佛教并没有参与介入。搞不清楚从什么时候开始,日本佛教被称为“殡葬佛教”了。 [详细]

| 末木文美士: | 圣一国师右眼失明,原来那是被师父用竹篦无数次痛打落下的“后遗症”。但我觉得有时这种接机施教方法未免过于暴力,您觉得呢? |
有马赖底:我们禅人并不这样看。刚才我已经谈到,我最初拜师森下和尚,虽然被他百般敲打,但是没有一丝一毫的怨恨情绪,反而觉得自己有一位难得的好师父。所以,挨打被踹,真是算不了什么。[详细]

| 末木文美士: | 您对日本的“天皇制度”是如何考虑的呢? |
有马赖底:提到天皇制度,我个人认为天皇制度是日本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一般来说,天皇制大体上属于“万世一统”,当今天皇属于“北朝”,“南朝”的天皇为“非正统”。实际上,所谓“万世一统”的天皇家系中混杂着朝鲜半岛民族的血统。最初在京都登基即位的天皇——恒武天皇的母亲高野新笠就出生于朝鲜半岛的百济。 [详细]
将“脑死”视为人的“死亡”,真是岂有此理!
末木文美士:以上,匆匆忙忙地请老师谈了谈您的人生,以及修行生活的宝贵体验。
有马赖底:那么,慢慢来吧!不用着急。
末木文美士:不能过多地占用您的宝贵时间啊。
有马赖底:哪里,哪里,我最近倒是很清闲。
末木文美士:那么,我们下面来谈一谈“禅与现代社会”这个话题吧。
有马赖底:好啊!请您随意地问吧。
末木文美士:最近,社会上关于“脑死”的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脏器移植”等问题的议论很多,不知您对这个问题是怎样看的呢?
有马赖底: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所谓“脑死”并不意味着人的“死亡”。
末木文美士:对!我也是这样认为。
有马赖底:最近“脑死”这个词汇在医疗现场和社会上十分流行。我们知道,虽然人的大脑“死亡”了,但是其肉体还在生存着,人还在呼吸。将“脑死”判定为人的“死亡”,这是违反常规道理的,岂有此理?
我认为,对“脑死”持肯定态度的那部分人还没有了解所谓“死”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在议论“脑死”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搞清楚“死”的概念问题。
末木文美士:我认为,最初基督教较为重视所谓“临终”或“死”这一问题,净土教的思维方式与基督教比较接近。例如,作为“临终医疗”,净土宗提倡开办所谓“寂灭道场”,即现代的“临终关爱医院”,开展减缓末期患者痛苦,给予关爱的援助活动。当然,这种富有社会意义的做法值得肯定,但是没有相关的积极进展。
关于“脏器移植”,有一部分佛教界人士认为,由于自身的死亡而拯救了他人的生命的行为,属于“菩萨行”,或“利他行”。例如,依靠“脏器移植”这一先进的医疗技术手段,可以使一个人的死亡换来五六个生命的延续。我个人认为,对于这种观点不能一概加以否定。
有马赖底:我也认为“脏器移植”这一医疗技术手段本身不能否定。
末木文美士:是吗?
有马赖底:但是,“脏器”并不是“物品”。贫困落后国家的贫困者向富裕国家的富人贩卖脏器,这是一个极为现实的社会问题。我认为这是一桩十分悲哀的交易。脏器不是“物品”,不是用来买卖的“商品”。
末木文美士:只是……
有马赖底:有些人认为由于一个人的死亡,而使五六个人的生命得以延续,这是一件值得提倡的好事。但是,我却认为这是一件令人无比悲哀和痛苦之事。
末木文美士:我能体会到您的心情。但是我认为,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如果有了这个脏器就可以生存”这一迫切的愿望。对于我来说,不能做到像您那样断言:“脏器移植绝对不行!”
有马赖底:您说得有道理。不论是学者还是医生都不会持绝对否定的态度,但是也不会赞成这是一件“好事”吧?我觉得不少人被所谓“有了脏器移植这一先进的医疗技术手段,就能够保证延续生存”这一舆论潮流所裹胁,而作出了“只要能救人命”的无奈选择。这是不足为取的错误判断和错误选择,这是一个必须加以纠正的大错误。如果不深刻地认识人类的“死亡”这一问题,这个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解决。
过去,由于医疗条件的局限,儿童的发病死亡率非常高。每当流行病泛滥,一家的两三个兄弟往往一同被病魔夺去生命。当时的人们即使想拯救弱小的生命也束手无策,所以,常说孩子是“自生自灭之物”。
我们如果比较一下丧葬仪式形式的变迁,就可以明了过去人们对待“死亡”的姿态。举行丧葬仪式之际,死者家属和亲朋好友往往聚在一处,鸡鸭鱼肉,大吃大喝,好像“过年过节”一样。吃喝过后,开始出殡送葬。出殡送葬的行列也是欢欢喜喜、热热闹闹,扬幡列队,装饰棺椁,敲锣打鼓,前往墓地。
过去都是土葬,坟墓分为埋葬尸体的墓冢和祭祀礼拜的墓冢。下葬后返回乡里后,又把祭祀礼拜的墓冢装饰得富丽堂皇。直到最近,在京都左京区的最北边,以及近江的朽木和若狭的多田庄一带,还可以看到这样的出殡送葬情景。
这也就是说,人的死亡是一件十分庄重严肃的事情,应该隆重地将死者送往黄泉。丧葬仪式可以说是人生最为重要的祭奠仪式。
以前,我曾经和身兼僧侣和医生的对本宗训(京都大学文学系哲学专业毕业后出家,38岁任临济宗佛通寺派管长。其后考入帝京大学医学系,同时辞去管长一职。现为临济宗“师家”,即具有指导修行僧的禅堂老师,内科医生——译注)在一起座谈讨论过这一问题。
末木文美士:您和他的座谈讨论内容汇集成了《禅的反击》这本书吧?
有马赖底:对。在座谈讨论中,我提到了刚才涉及的“孩子是自生自灭之物,死了,还可以再生”这一话题,同时还谈到了人的“寿命”问题。被病魔夺走了亲生子女,陷于无比悲痛之中的父母经常用“这就是命啊,没办法呀!”这句话来宽慰自己。如果不这样想的话,就难免陷于过度悲伤之中,难以自拔。
末木文美士:如果说上了年纪的人“尽享天年”,这很容易接受,但是对于幼儿,年轻人也使用“寿命”一词,来宽慰自己和他人的悲伤心情,这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恐怕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人们的头脑中自然而然地产生“想方设法来挽救生命”这种想法也是无可非议的吧?
有马赖底:我们不能笼统地用“寿命”这两个字来认识和概括人的死亡现象,因为有三岁的寿命,也有一百零五岁的寿命。
师父与徒弟之间仿佛流淌着一股电流。
末木文美士:下面,想请您简单地介绍一下所谓“禅修”。说老实话,我个人也曾经有过一个阶段坐禅的体验。
有马赖底:是吗?您是在哪里体验坐禅呢?
末木文美士:在我的老家山梨县,我们家祖上是“时宗”(镰仓中期的净土宗僧侣一遍开创的宗派,为净土宗门流派之一——译注)的“檀家”。
有马赖底:是不是一莲寺?
末木文美士:对,一莲寺的规模很大,仅次于藤泽的时宗本山游行寺,现在已经独立了。过去,“游行上人”(行脚各地、念佛布教的时宗僧侣——译注)一生必须要去一莲寺参拜一次。
有马赖底:但是您没有皈依祖上信仰的时宗,而转向了禅门。
末木文美士:我上大学的时候,经常去“东京八王子”的广园寺参禅,广园寺属于临济宗南禅寺派。
有马赖底:哦,去亲近丹羽老师了?
末木文美士:对,拜丹羽慈祥老师为师,参禅问道。但是我生性懒惰,“接心”的第三天就跑了出来(笑)。不管怎么说,可能禅最为适合我的秉性,上大学期间一直断断续续地参加了坐禅会。另外,还亲近过原来常住广园寺,现在担任向岳寺管长的宫本大峰老师。
有马赖底:哦,宫本老师呀!
末木文美士:对,多年来一直承蒙宫本老师在各方面指导教诲。
有马赖底:那太好了!
末木文美士:一般的门外汉都认为,禅宗寺院的修行生活十分严格,请您简要地介绍一下好吗?
有马赖底:入门最初要过“庭诘”一关,前后共三天,然后是“旦过诘”,即要在“旦过寮”过上四天,合在一起整整一周。经过长达一周的磨炼后才许可“参堂”,即进入禅堂,开始正式的修行生活。
末木文美士:听说“庭诘”十分难熬。
有马赖底:“庭诘”那三天的确非常辛苦。参堂,就是被允许进入禅堂内,加入“云水僧”的行列。当年,我穿上袈裟后便被带到了大津枥堂老师的面前。枥堂老师就像一块巨大的岩石矗立在我的面前,压得我喘不过一丝气来。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是被枥堂老师浑身所散发出来的深邃洞察力和雄浑的魄力压倒了。不过,当时我就暗下决心:“选择了这位师父可太好了!在他的指导下,无事不成,无论任何艰难困苦我都一定能挺过去。”
我们僧侣肩负着为死者亲属的“今后”出谋划策,尽到给予心灵护理的职责和义务。
末木文美士:说起日本的佛教,无论如何都抹不掉与“殡葬”的联系,因此日本佛教被称为“殡葬佛教”。举行殡葬仪式之际,一般人家总是要请和尚来念经超度。近些年来,委托给殡仪公司的家庭也在逐渐增多。还有一些人家选择“直葬”,即将死尸送往火葬场,然后取来骨灰下葬。不过,我个人认为所谓“殡葬佛教”的社会作用比较重要。
有马赖底:说起殡葬仪式,现在,随着殡仪公司的日益专业化,我们僧侣往往作为“配角”登场,采用这种形式的殡葬越来越多了。
末木文美士:您说得很对。现在,殡葬仪式越来越专业化了。
有马赖底:我认为这种形式也不错。僧侣主要负责为死者家属的“今后”出谋划策,给予心灵的护理和关爱。
其实,过去殡葬仪式都是由专业公司操办,佛教并没有参与介入。搞不清楚从什么时候开始,日本佛教被称为“殡葬佛教”了。本来,为死者临终之际“送终”是佛教徒的义务,当然这也是以当事者的亲属为对象。
一般说来,一家之长去世后,家庭内部总要出现不同程度的矛盾或争斗,比如谁来继承家业,财产如何分配等等。在殡葬仪式上,我们一般仔细地观察现场的实际状况,然后适当地向死者的亲属们建言献策。这就是僧侣的社会职责,也是心灵的护理和关爱。
但是,能够游刃有余地胜任这一神圣使命的僧侣越来越少了,也就是说和尚的职业水准越来越下降了。这是佛教界当前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换句话说,只能充当配角,只是领取“出场费”的和尚过多了(笑)。相反,现在许多殡仪公司不仅担负起了心灵的护理和关爱工作,而且完成得还非常出色。这个社会现象对我们佛教界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和鞭笞。
末木文美士:您说得很对。家父三年前病故的时候,就请了殡仪公司,整个仪式非常圆满顺利,大家都非常满意。
有马赖底:听说这些殡仪公司都非常用心去做殡葬仪式。
末木文美士:对!
有马赖底:我还听说,最近殡仪公司还在殡葬仪式上提供流行音乐播放等服务项目。
末木文美士:说到底,殡葬仪式就好比演戏。殡仪公司的职工就是演出家人的角色。
有马赖底:这么说来,僧侣的“演出费”数额也是由殡仪公司决定的了?
末木文美士:对,就是这么回事。一般来说,殡仪公司要向客户建议大约需要支付诵经的法师多少费用等。因为,客户一般不太清楚市场的行情,所以觉得这种做法很方便。可是这样做的话,难免招致僧侣商业化之嫌。
有马赖底:我绝对不赞成这种做法,这种做法有失妥当。
我也时常去殡葬仪式上为已故信徒诵经超度。上一次,有一对年轻的新婚夫妇贷款购置了房产后不久,万万没有想到丈夫突然病故了。我参加了他的殡葬仪式,为他诵经超度。考虑到这一家的处境,以及还要继续偿还贷款等实际情况,我于是就叮嘱死者的亲属:“这份礼金绝对不能收!”
那位夫人泣不成声地向我反复道歉:“真对不起!真对不起!”我平心静气地对她说:“你今后的人生道路还很长,可能还会比较艰难。虽然你的先生不在了,但是你一定要努力坚强地生活下去!”她听了我的这番话后,热泪不止,频频点头鞠躬。
我觉得这种事情不能简单地用金钱来处理,这就是我们佛教徒应该发挥的社会作用。
末木文美士:听了您讲的这段亲身经历,我的心头也不禁为之一震。现在,不少僧侣往往做不到这一点了。
圣一国师单目失明后,方才觉悟。
末木文美士:最后,我还想再一次向您请教一下“公案”的问题。我最近打算整理汇集一下“公案”方面的研究课题,正好利用今天这个机会,请教您几个问题。
一般来说,公案中没有所谓“道理”或“理由”。但是我一直在琢磨,是否能够从理论角度来考虑和认识公案呢?
铃木大拙先生经常引用《无门关》第43则“首山竹篦”这一公案。这则公案的大意是:不可说是竹篦,又不可说不是竹篦。在理论上讲,就是以所谓“排中律”为前提条件。也就是说,或者肯定,或者否定,而毫无中间道路可走。以这一理论为依据,而欲超越这一理论。由此看来,这则公案最初就明显地意识到了所谓“理论”问题。但是,最近的数学研究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就是所谓“排中律”并不一定存在。换句话说,就是存在“肯定和否定都不存在”这一命题。
有马赖底:哦,是吗?
末木文美士:如果这一观点成立的话,最尖端的数学也好,逻辑学也好都在向禅接近靠拢。所以,我感觉如果把禅与数学和逻辑学结合起来研究的话,将是一个十分吸引人的课题。
有马赖底:您看过东福寺开山祖师圣一国师的顶像,就是肖像画吗?
末木文美士:就是室町时代中期著名的佛画家兆殿司明兆绘制的那幅肖像画吧?画得十分逼真……最近,学术界对圣一国师非常关注。
有马赖底:对,圣一国师就是圆尔辨圆,肖像画上的右眼失明了吧?
末木文美士:对,的确是这样。
有马赖底:您知道圣一国师的右眼是怎么失明的吗?那是被师父用竹篦无数次痛打落下的“后遗症”,师父手中的竹篦伤了圣一国师的眼睛。
手操竹篦的就是圣一国师的师父无准师范和尚。无准师范和尚把首山禅师曾经向修行僧提出的“首山竹篦”这一公案交付给自己的徒弟圣一国师。这则公案,就如同您刚才介绍的那样:“虽然是竹篦,但是不可说是竹篦,也不可说不是竹篦”,找不出所谓“答案”。这是一则闻名禅林的难题。无准师范和尚就是把这一难题交付给了不远万里前来径山拜师求学的日本僧圆尔。他对这位年轻有为的留学僧寄托了无限的期望。
接受了这则公案以后,圆尔从早到晚呕心沥血,投入坐禅修行的实践之中,但是无论如何都寻觅不到理想的答案。即使如此,圆尔还是定期怀揣着自己的答案前往无准师范座下禀报禅修结果。有一天,无准师范手操竹篦,不分青红皂白照着前来禀报的圆尔身上就是一顿抽打,被打得几乎气绝的圆尔终于大彻大悟了。从此以后,圆尔继续在无准师范门下修行,三年后学成归国。圣一国师圆尔辨圆归国以后,日本禅林翻开了崭新的历史篇章。
末木文美士:这么看来,从这则公案里找不出所谓“理论”的踪迹呀!?不过,这种接机施教方法未免过于暴力。
有马赖底:但是,我们禅人并不这样看。刚才我已经谈到,我最初拜师森下和尚,虽然被他百般敲打,但是没有一丝一毫的怨恨情绪,反而觉得自己有一位难得的好师父。所以,挨打被踹,真是算不了什么。
身为禅师,是出于及早把手下弟子培育成才的想法而下手敲打徒弟的。无准师范禅师正是因为看准了圆尔将来能够成为挑起日本禅林栋梁的首屈一指的禅僧,所以才把“首山竹篦”这则难题交给了圆尔,目的在于使自己心爱的弟子大彻大悟,早日成才。
末木文美士:所以,即使打瞎了一只眼睛,也在所不惜……
有马赖底:对,一只眼睛失明以后,圆尔方才大彻大悟的。我认为,无准师范这位古德是想把禅的真正面目通过圆尔传往日本,所以,通过痛打唤醒了圆尔心中沉睡已久的灵性。
末木文美士:那么,说到底这是师徒之间的无比牢固的信赖关系呀!您和您的师父森下和尚之间可能也存在着这种信赖关系吧?
有马赖底:您说得很对,我们师徒之间可以说就是这种关系。
末木文美士:听您这么一介绍,我更想亲眼看一看森下和尚送给您的那本《绿色的魔术》了,可惜今天……
“天皇制”是日本文化的一个重要范畴。
有马赖底:所以,我们可以说禅的精神是一个极为丰富的世界。
末木文美士:就是呀!的确可以说是广纳百川,泽惠四海。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既令人欢喜又使人畏惧的世界(笑)。那么,我们转入正题吧。有马老师,您对日本的“天皇制度”是如何考虑的呢?
有马赖底:您提的问题很“正点”啊!是不是因为我和当今天皇是朋友的缘故吧(笑)?
末木文美士:听说您和当今天皇曾经同窗共读?
有马赖底:那是学习院幼儿园时代的往事了。我当时被选为当时的皇太子,就是现任天皇的陪读伙伴,每天在一起荡秋千、刨沙坑。至于为什么会选中我,我可不太清楚其中的缘由(笑)。
提到天皇制度,我个人认为天皇制度是日本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一般来说,天皇制大体上属于“万世一统”,当今天皇属于“北朝”,“南朝”的天皇为“非正统”。
实际上,所谓“万世一统”的天皇家系中混杂着朝鲜半岛民族的血统。最初在京都登基即位的天皇——恒武天皇的母亲高野新笠就出生于朝鲜半岛的百济。
我认为,应该继承和保留天皇制度,因为天皇制度本身是日本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使不必追溯到神武天皇(史籍传承的神话中出现的日本第一代天皇,天照大神后裔。传说他建立了最早的大和王权,为日本开国之祖与天皇之滥觞——译注)时代,从天智(673—686在位)、天武天皇(668—671)时代算起,天皇制度已经连绵不断地传承了一千数百余年。
当年,由中国和朝鲜半岛传入的外来文化就是日本文化的源泉。很多外来文化的“外形”至今还完整地保留着。比如京都的“冷泉”这一家族,就是近乎奇迹般地繁衍传承了下来。冷泉家族完整地保留着天皇家族一年四季日常生活中的传统仪式,并且古为今用。有关的历史文献记录也都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前一阵子,是否设立“女帝”一时成为日本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当时的首相小泉纯一郎曾提出建议:“能不能想方设法把‘爱子’(现皇太子的长女——译注)改定为皇位的合法继承者?”并尝试改动《皇室典范》。
我们知道,《皇室典范》制定于明治时代,前后历时二十余年。而小泉纯一郎却打算利用三个月的时间加以改动。根据日本的“新宪法”(昭和二十二年开始实施——译注),虽然天皇仅仅为象征权位,但我认为即使天皇制度仅仅是一个象征,这个制度也应该加以保留和继承。这不是设立“女帝”与否的问题,也就是说不是什么单纯的“男与女”的性别问题,而是如何保持皇室传统,即如何保持日本传统文化的大问题。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设立“女帝”制度。日本历史上,持统天皇、元明天皇、元正天皇,还有江户时代的后樱町天皇等都是女帝。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排斥女帝制度。
我刚才提到的“冷泉”这一家族,几百年来一直将皇室的新年、歌会、节分,七夕等传统节日和祭祀活动原封不动地继承保存了下来。我们通过冷泉家族一年四季的日常生活,就可以概括地了解日本文化的大致轮廓。
我们必须大力地保护诸如此类的日本传统文化。这不是一个保留不保留天皇制度的小问题,而是一个如何保护和继承日本传统文化的大问题。
和尚,挺身而出!
凤凰网华人佛教联合多家出版社,将持续开展“开卷有益”这项有奖赠书结缘活动。
微博参与:
1、关注凤凰网华人佛教微博。
2、在话题#觉斗#里@ 你的三名好友!就有机会获得凤凰网华人佛教为您准备的礼物了。
微信参与方式:
1、首先,需要您关注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我们微信公众账号的名称是:凤凰网华人佛教。
2、将#觉斗#活动信息分享至朋友圈,截图后通过微信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奖了。

责任编辑:马本州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凤凰网保持中立